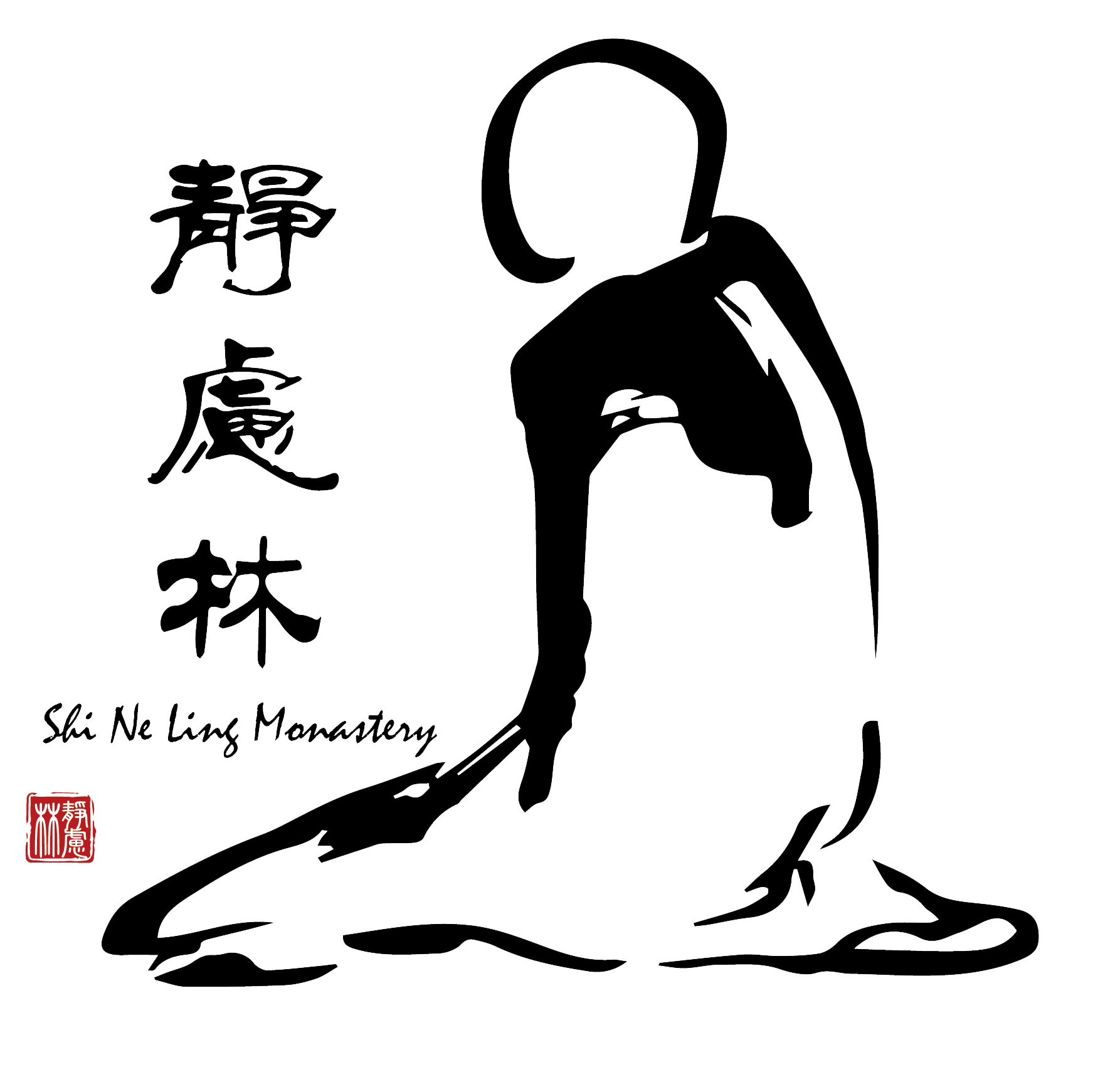阿姜給尊者
2019年3月14日A|第十一屆泰國四念處禪修課程
聽錄整理|法音錄

在座的各位,大家好!
我們剛才的活動叫做「串愛之花」。花在泰文裡的名字就是愛。
愛有幾種形式?在中國有幾種愛?三種?有覺得比這更多的人嗎?有幾種?(學員回答)沒關係,師父接下來講在佛教裡愛分成三種形式,但如果把它再濃縮一下,就只剩下兩種。
第一種形式的愛是大家一般都能理解的男女之間的那種愛。這種形式的愛是希望別人可以為自己帶來快樂,或者是想獲得那個會給自己帶來快樂的事物。比如看到宋(翻譯)很帥,很有才能,做事情非常認真,然後就想把他佔為己有,變成自己的,把他佔為己有之後,他就會給自己帶來快樂。這屬於帶著貪欲的愛。
如果希望外在的人事物能為自己帶來快樂,佛教裡的專業術語稱之為貪欲。比如阿姜巴山在講法的過程中提到某一位老師,他是所有指導老師中最年輕的一位,他帥呆了,而且他的腦袋瓜子極其聰明,學歷也非常高,而且還是一個富豪,最關鍵的是他還單身。
哎呀,這就是我的菜!臉都沒有看到過,但是心裡已經在想一定要變成他的主人。這稱為貪欲。如果我們聽完之後並沒有想得到他、把他佔為己有,這稱為沒有貪欲。
假設我們聽到這樣的介紹:有一位指導老師,他是所有指導老師中年齡最大的。聽到之後,因為他年齡已經很大了,我們就沒感覺。而且他不怎麼聰明,很蠢,我們心裡就開始幾乎不想沾邊了。而且他非常散亂,我們心裡就會想:這種人根本不值得親近,不值得認識。而且他現在出家了。哦,他出家了,讓他出家吧,出家出家!這樣的人千萬別還俗,這樣的人我不需要,我不需要。這樣的話就沒有貪欲。如果他有非常好的品質和特質,我們愛上了他,希望他可以為我們帶來快樂,這稱為貪欲。
還有另外一種形式的愛。假設我們愛宋,但是我們並沒有期待把他佔為己有,我們只是有這樣一個願望,希望他可以快樂。這樣的愛不能稱為貪欲,這樣的愛稱為慈悲。
—般的人都會籠統地把這兩種形式稱為愛,但是因為它們背後真正的動機不同,所以在佛教裡的專業術語就不同。
還有另外一種形式的愛,它不是對人的愛,而是對工作的愛。
比如我們很愛自己的家,希望自己的家可以很乾淨、很舒適,我們就會很勤奮地去做衛生,做一些調整和安排,這稱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是帶著愛心在做的。
比如對樹木的愛,我們希望樹可以慢慢地茁壯成長,最後都能夠開花結果。一旦對樹木生起了這樣一份感情,我們就會想方設法讓它達到自己預期的效果,我們就會努力地去培土,去施肥,去澆水。
因為希望這棵樹可以茁壯成長,那樣的愛稱為具有善法欲的愛。事實上,我們是愛這棵樹的,但是我們真正的動機是希望精進地做一些事情,讓這棵樹可以成長。
特別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就是菩薩愛一切眾生,他愛一切眾生是出於慈悲心,這屬於正常情況下的一種愛。他愛眾生,希望眾生可以從苦海裡跳脫出來,佛教裡的專業術語稱之為悲心。
他去弘傳佛法,教導眾生離苦的方法,眾生按照他的教導去實踐之後,有次第地抵達了不同級別的法。當眾生獲得這樣的成就之後,他心裡會非常喜悅,佛教裡的專業術語稱之為隨喜心。
也就是說,愛可以分為屬於善法的愛和屬於不善的愛。
我們對對方的愛是希望對方可以給我們帶來快樂,那是屬於含有不善法的愛,因為每一次這種感覺生起,每一次我們內心都會有苦。
每一次貪欲生起的時候,我們的呼吸都會變得不正常,變得急促起來。因為這種愛的背後是有很強的貪欲在驅使的。但是如果那種愛裡是含有善法的成分在的,我們的心就不會處在那樣的狀態。
—個有慈悲的人的心是很舒坦的。在他有悲心的時候,並不是說他就苦了。在有悲心的時候,看到別人正在受苦受難的時候,他是無法袖手旁觀的,一定要去幫對方一把。其實那仍然屬於慈心,只是慈心的對像是一個正處在苦難中的人,所以就有一個專業術語,稱為悲心。
如果我們的心處在平常的狀態,這是一種形式的愛;另外一種形式的愛是我們的心靈處在下墮的狀態;還有一種形式的愛是我們愛完之後,獲得一些成果之後,我們的心靈水平是上升的。所以,從心靈所處的狀態而言,愛其實分三個級別。
拿一個小孩子的情況來作比喻。比如這個小孩子不苦不樂的時候,我們對他的愛就是處在慈心的狀態。如果這個小孩子考試不及格,他很悲傷、很傷心的時候,我們去安慰他、安撫他,這屬於悲心。安撫完之後,他的考試成績有所提升,他很高興的時候,我們也會很喜悅,那個時候我們對他的愛稱為隨喜心。對,就是我們平時說的那個隨喜。
有人做完功德之後,我們對他說隨喜功德,那其實就是慈悲喜捨裡的喜。這樣的愛是屬於帶著善心的愛。
師父本人在這裡特別想重點介紹的是帶著善心的愛之中的帶著善法欲的愛。要想能夠對善法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最好把它跟欲望作一個對照。
欲望的意思就是想獲得結果。欲望只是一味地盯著結果,希望得到結果,而善法欲是把自己要得到的那個結果作為目標。他清楚地知道要想達到那個目標,必須要做什麼樣的因,他會非常勤奮地在因地上去努力。
比如我們來學法修行,我們聽高僧大德、老師們開示完之後,就會想獲得涅槃,獲得道與果,我們覺得自己太愛佛教了,期望可以獲得道果涅槃。由欲望在背後驅使的狀況就會是一直想著我要涅槃,我要涅槃,但只是一直躺在那裡,想著什麼時候涅槃才可以來。只是躺著還不夠,一定要進入美夢,萬一不小心就在美夢裡見到涅槃了呢?然後也會發現光做夢還不行,一定要打坐,多多地打坐,讓自己一動不動的,以便萬一一不小心,啪的一下涅槃就現前了!一旦心跑了,這個不可以,你馬上回來,如果你跑了,就不可能得到涅槃,於是馬上拼命地把它拉回來。
這樣的狀態稱為有欲望在背後驅使,想獲得結果,卻不願意在因地上去努力。我們並沒有在涅槃的正確的因地上去用功的時候,即便我們看起來很勤奮、很精進,那仍然不能被稱為善法欲。
含有善法欲的愛是帶著智慧的愛。對涅槃這個結果是有期待的,是有這樣一個期望的,但是是去透過學習抵達涅槃的正確的因是什麼,認真學習之後,然後在那個相應的正確的因上去努力、去精進。
透過學習了解到要想抵達涅槃,一定要有戒、有覺性、有禪定、有智慧,然後就會努力地去持戒,不讓自己通過身與口去傷害任何人。
至於覺性,我們就需要去了解和學習究竟是什麼樣的因會讓覺性生起。透過學習了解到什麼樣的因會讓覺性生起之後,我們就會在相應的因地上去用功。明白到真正讓覺性生起的近因是心能夠牢牢地記得那些境界或狀態之後,我們就要開始訓練自己,不斷地去常常地去看到那些境界或狀態。
最開始我們往往喜歡去覺知那些比較好的境界跟狀態,一旦碰到那些所謂的不好的境界,我們就會不喜歡。但隨著學法、修行的深入,我們就會了解到那些不好的境界跟狀態依然是境界跟狀態,我們的心就會慢慢地開始越來越願意去接受它們,願意多多地不停地去緊隨著覺知它們,於是在覺知的過程中就擁有了善法欲。
常常地覺知自己,最後心就能夠牢記那些境界或狀態。因為擁有含有善法欲的心,有常常地去覺知自己,最後就會獲得正確的覺性。
接下來是禪定,那什麼是禪定生起的近因呢?我們就一定要了解到快樂是禪定生起的近因,而且這種快樂裡是帶著覺性的,是有在覺知自己的。而不是坐著看海,一直是快樂的,心一直是往外送的,不是那樣的狀況。也不是打開電視或網絡,看一些電視劇或笑話,哈哈哈哈哈……那並不是真正的快樂。一定要是含有覺知自己的那種快樂,也就是說我們跟心的「臨時的家」在一起的時候,是以一顆輕鬆快樂的心待在這個「臨時的家」裡。
但如果要想訓練心安住,就必須要覺知到心,因為禪定真正的意思是指心安住的狀態。心跑掉是心沒安住,如果我們及時地知道心跑掉,知道心沒有安住的狀態,心就會剛好安住那麼一剎那。但是一定要帶著一顆快樂的心去觀,而不是一直期待心必須一動不動的,如果那樣,心一旦跑掉,我們就會有一些不舒服,因為它跟我們的期待不一樣,我們就會有苦生起。
要想讓我們的心在看到心走神、心跑掉的時候有快樂,就一定要從一個學生、一個學者的角度去看。一顆真正的學生的心是懷著一份學習的心態的,無論境界是好還是壞,都本著一份學習的心態去看。就好比我們要去了解某一個動物的生活習性,無論這個動物的表現是好還是壞,如果我們去觀察,它全都會變成我們的一種知識和了解。
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去馴服這個動物,而是要了解這個動物自然狀況下的生活習性。如果我們的目標是馴服這個動物,讓它溫順下來,那麼一旦它的表現跟我們所期待的不一樣,我們就會不滿意。如果我們的用心是這樣的,當它真正呈現它自然的狀態時,我們往往就會不喜歡,因為它真正很自然地呈現出的狀態往往是我們認為的所謂的不好的狀態。
但是如果我們懷著一份學生的心態,無論它是好還是壞,每一次它呈現出來,每一次我們了解到,我們都會得分。所以,在每一次覺知、每一次了解和看見的時候,我們都會懷著一份快樂和喜悅的心。
在我們看到心跑掉的那一剎那,心就不再跑了,就會變成心安住的狀態。心在安住的那一刻,其中本身是含有覺性的,但是在那一刻,真正比較明顯的是禪定。
智慧也是相同的。智慧生起的近因是正確的禪定。也就是說,心一旦安住之後,就真的可以如其本來面目地去看到那些境界或狀態。
心安住之後,如果來觀身,就會看到身是身,或者是一堆什麼東西,然後知者就會分離出來。在心安住的那一剎那來觀身,名和色就會立馬分離。
那一刻發生的時候,也許並沒有文字去描述究竟什麼是什麼,但是會清楚地照見到身體是屬於身體的部分,身體是被覺知、被觀察的對象,還有另外一部分——作為觀者的心。觀者的心裡也許還含有邪見,以為那個心是我,但是會清楚地照見到身體是被觀察、被覺知的對象,身體不是我。
在心安住的時候,如果看到煩惱習氣,就會看到煩惱習氣僅僅是一種名法,它跟觀者的心完全是不同的部分。無論你是否知道這個煩惱習氣的名字,你都會清楚地知道它跟心完全是分離的。
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往往會看到煩惱習氣不是我,但依然會覺得那個知者的心是我。繼續訓練下去,繼續去發展覺性,去修習禪定,那些境界和狀態就會不停地教育我們,最後我們就會發現心一會兒變成知者,一會兒變成想者,一會兒變成緊盯者,不停地如此交替。
所有的境界和狀態最後就會來不停地教育我們的心,讓我們的心變得聰明,最後我們就會看到事實:無論是能觀還是所觀,它們都只是自然生起的現象,它們各有各的分工,各有各的職能,裡面沒有個我。到了這個程度,就稱為得到了第一階段的法,佛教裡的專業術語稱之為初果須陀洹。
要想來到這個階段,一定要有精進、忍辱,不斷地去培養、去提升我們的戒定慧。要想擁有這些,就一定要有一個基礎的東西,也就是善法欲。
我們看到了我們要得到的結果的好處,我們也清楚地了解到要想獲得那樣的結果,必須播種什麼樣的因。真正動手實踐的時候,我們就會對自己的心和身投入很多的注意力。尤其是那些散亂型的人,他們要重點學習的是心。
佛陀有過一段開示,在早期的禪修中,師父已經講過了。這是佛陀對那些心很散亂的師父們講的,他說心有這樣一個特質,也就是它會跑得很遠。
我們的心會跑得很遠嗎?心可以環遊全球,甚至可以沖出地球。比如嫦娥奔月,即便原本是在這個地方,但是她也可以奔到月亮上去。
心可以跑得非常遠,但是它一次只能去一個剎那。它要想跟嫦娥一起奔月,先是在這裡。它是一個片刻、一個片刻的。
知道心去到月亮上了,知道的那顆心就已經是另外一個片段了。知道的那個剎那的心也會滅掉,然後就繼續去想別的事情了。比如我們心裡會有類似於配音的聲音,說剛才去散亂了,那本身已經是在散亂了。
心是不停地處在生滅的狀態的,而且它一次只能生起一個剎那。在真正覺知的那一念,心是沒有說什麼的。去界定剛才散亂了,那已經是另外一個片刻了。能明白嗎?它們是不同的片刻。
心看到宋,生氣了,那是一個剎那。另一顆心要想生起,這顆生氣的心就必須先滅掉。事實上,並不用去處理它,使它滅掉,它本身就是生滅的。只是說在訓練的階段,我們需要有一點點人為、刻意的成分去知道剛才的心是生氣的。
假設這一念心看到宋,生氣了,然後滅掉。接下來新的一念心生起之後,我們刻意地去看前一念心是生氣的,這個新生起的一念心裡是帶著覺知的。
在它看的那一瞬間,它的工作已經結束了,還來不及說話。要想去界定剛才生氣了,或者念誦所謂的「生氣啦,生氣啦」,或者看到剛才有瞋心了,一定要等這顆覺知的心先滅掉,才可能出現後面的這些。
所以佛陀對那些很散亂的師父們開示的偈子,就是說心會跑得很遠,但是它是一個剎那一個剎那地生滅的。有兩種特質了。
第三種,它無形無相,它屬於名法。意思就是說我們無法用眼睛看,或者用耳朵去聽心究竟在哪裡。這樣是不會知道的。或者去聞心在哪裡,也找不到。我們只能用同樣屬於名法的東西去感知它,這樣的名法稱為覺性。
事實上,在訓練的早期,稱為覺知自己。隨著我們不停地去訓練,直到我們的心最後能夠牢記境界,牢記到當這個境界生起之後,覺性就會自動生起,那時候就屬於能夠記得、能夠憶起境界,這才是覺性真正的定義。
佛陀還教導要去看心的另一種特質,也就是第四種特質。
複習一下,心的第一個特質是跑得很遠,第二個是什麼?每一個剎那只能生起一次。第三個是它屬於名法。一旦說到心是無形無相的,是屬於名法,那怎麼才能看到它呢?所以佛陀就開示了它的第四種特質。佛陀說它在洞裡面,意思就是說身體是心的洞穴。
既然它就躲在這個洞穴裡,所以起步的時候就可以先觀那個洞穴,也就是觀身體。比如觀呼吸,在心走神的一剎那,就會看到心走神,在心跑掉的那個剎那,就會看到心的跑掉。之所以知道剛才我們的心走神了或者跑掉了,是因為我們剛才就守在那個洞穴門口。
但是這個洞穴有六個出口。這六個出口是哪些?眼耳鼻舌身心。它最頻繁地跑出去的那個出口是心,所以我們就著重守在心門這裡,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不去觀其他出口了。心呆在洞穴裡,這個洞穴就是身體。因此,我們依賴於這個身體,是為了了解心究竟是什麼樣的狀況,心會從哪個出口出去。
為了觀得簡單一點,我們就不用去守六個出口,直接去觀心那個出口就可以了。觀呼吸之後,心一旦跑去想了,及時地知道。覺知之後就立馬再次進到這個洞穴裡來,而且不需要把剛才的那顆心拽到洞裡去,因為剛才的那一念心已經滅掉了。剛才已經講過了,佛陀所開示的心的幾個特質中的第二個就是它一次只能生滅一次。
我們繼續去觀身、觀心。在觀身的那一剎那,是一個片段,很快我們就會走神,在走神的那一刻,又是另外一個片段了。在覺知的時候,覺知是另外一個片段。在我們覺知的那一個片段,前面的迷失已經滅掉了。我們並不用把過去的那顆心再拽到那個洞裡去,因為這樣的工作已經不存在了。而且覺知的心也會滅掉。無論是迷失的心還是覺知的心,我們都根本無需再對它們做什麼了,我們只需要讓那個洞裡再重新生起一顆新的心就可以了。
我們隨時準備好去學習和了解心接下來準備幹什麼,以一份學生的心態,有善法欲在背後驅動我們不斷地去對我們的身心進行學習和了解。
能記住嗎?心有哪四種特質?好,來複習一下。它跑得很遠;它是一剎那一剎那地生滅的;它是名法,只有覺性才能捕捉到它;它藉居在這個身體裡。佛陀並沒有開示到這裡就結束了,佛陀還開示道:如果我們不停地去學習、認識和了解這顆心,最後我們就會脫離魔掌。
那些非常散亂的出家眾在聽完佛陀的這一段開示之後,就證悟了初果須陀洹。誰已經開悟了?噢,可能必須要用巴利文。巴利文應該不用翻譯。
(尊者念誦了一段巴利文)
Dūraṅgamaṃ ekacaraṃ asarīraṃ guhāsayaṃ; Ye cittaṃ saṃyamessanti, mokkhanti mārabandhanā.
這是巴利文。因為當時聽佛陀講法的是印度人,所以佛陀就會用當時印度人能聽懂的語言去為他們開示。
當時的那些弟子們為了能夠很容易地記住佛陀的開示,他們往往會像作詞一樣對開示作一些修飾,讓它聽起來更加優美,類似於我們做早晚課的時候,用的並不是我們平常說話的方式。是這樣的狀況,大家聽,(尊者用巴利文唱誦經文)這就是唱誦的方式,讓它聽起來非常優美,便於記憶。
【完】
法音錄聲明:
文章轉錄自微信公眾號「禪窗」法布施的音視頻。為便於閱讀且符合書面表達,我們對其進行了後期編輯校對,內容未經課程老師及譯者審校,準確性未得到確認,若存在任何錯誤或偏差,完全歸責於整理者,望讀者知悉與明辨,並請不吝指正。本文嚴禁用於任何商業用途,嚴禁擅自節選或改編,轉載請註明出處。
音頻來源:禪窗
視頻來源:Dhamma.com
附錄:
Dūraṅgamaṃ ekacaraṃ asarīraṃ guhāsayaṃ; Ye cittaṃ saṃyamessanti, mokkhanti mārabandhanā. 遠行與獨行, 無形隱深窟 。 誰能調伏心, 解脫魔羅縛。 ~法句经第37偈
注解:
dūraṅgamaṃ:心沒有移動到東方等,甚至連蜘蛛絲的寬度也沒有。然而,他卻可以接收遠方的對象。因此,心是遠行的。
ekacaraṃ:在同一剎那,只有一個心生起,不是一堆心同時生起。當生起時,心單獨生起,滅時,另一心生起。因此,心是獨行的。
asarīraṃ:心沒有身體的構造,也沒有色等區別。
guhāsayaṃ:心是藉著心所依處色(hadaya-rūpa)生起。guha是指由四大組成的這個窟。
ye:男人、女人、居士或其他已成為宗教的修行者。
cittaṃ saññamessanti:不讓未生的煩惱生起,且去除已生起的煩惱,即是調伏心。
mokkhanti mārabandhanā:因為沒有煩惱的繫縛,這些人將遠離三有之輪,即是魔羅的繫縛。